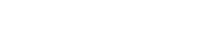“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他露出一个象征着危险信号的笑脸,烫人的指尖在她的脖颈滑走。
许尤夕怕得止住了呼吸,预测在下一秒自己的脖子就会被他掐住,掐到濒死才松开。
她还是不愿意说出求饶的话。
言易甚被脑中的两种指示拉扯着迟迟不动作。
一种让他赶紧动手,掐住仿佛稍微收力就会断掉的脆弱的脖子,让她知道惹怒自己的下场,以后再也不敢对他说出这种话。
另一种却不允许他做出暴行,好像他只要敢那样做,她就会彻底离开自己,再也不愿意陪在自己身边。
最后也没有那么做,理智占了上风。
言易甚的手掐住的是她的那截腰,把狠劲发泄在了下面相连的地方。
肉体快速碰撞的声音和压抑的哭音混合在一起。
之前从来不会为此停止的言易甚停了下来,他把高耸的物件弄出来,抱着她进了浴室。
热水从头顶直下,被紧紧圈住腰肢的许尤夕挂在他身上,断断续续吸入的湿热让她很想蹭蹭言易甚。
她浑身都没力气了,还想让听不出字句的声音从自己的喉咙慢慢流泄。
言易甚很高,也就有一双与身高相符的大手,很美观的手,指节修长,骨节较粗,给冷白色的手增添了色气。
那双大手揉搓着她发着莹白光芒的肩头,又往下揉她单薄的背。
许尤夕听见他很轻的一声叹气:“我给你一次机会,你和我说清楚原因。”
他没有抱着她淋浴太久,很快就扯了条干浴巾给她,把她抱进房间。
裹好浴巾的许尤夕看见他也扯了一条用来遮住下半身的光景。
那肿胀粗硬、丑陋的怪物依旧保持着兴奋的状态。
许尤夕不由自主地双腿发软,结合他刚刚的那句话,她就盯着他那根被浴巾遮上后,还是明显凸起的那块。
“我的鸡巴好看吗?让你一直盯着,哪有人像你一样,说要离婚,却还盯着前夫鸡巴移不开眼的?”
桃粉的脸蛋彻底通红,但很快,她的脸色一下变白。
她以为还要多纠缠一下,甚至说自己要吃些苦头。
可是,他就这么平静地带着自己洗了个澡,自称起前夫。
她一时间不知道是失落多还是开心多。
但可以确定的是,听出他愿意离婚的意思,让许尤夕很高兴。
“好了,该你说说原因了,我想不明白,是什么让你一直在找机会离开我?”
言易甚用手抬起她的下巴。
比最青涩时的她还要漂亮,还要可怜,看了十年越看越喜欢,越看越想亲吻。
她从十八岁起给自己操了,可怜巴巴地对自己一见钟情,到底是怎么选择要离开的?
被拉上窗帘的房间里开了灯,灯光从上倾斜了下来,言易甚俊美的脸上分布了几块阴影,他的眼睛里又没有属于人的温度,恍若神邸。
许尤夕时常会看着他,混乱的想:神不给人降福,却选择拉她下地狱吗?
她没有偏移视线,声音还是有些颤抖,她说:“我不是只有你了,我有妈妈,有烛烛。”
言易甚听她给的这个原因,有些恼火,突然压低身子,和她接吻。
侵略的意图太过明显,被疯狂汲取氧气的许尤夕死命推他,因为慌乱忘了呼吸,她更缺氧了。
她身上的浴巾就在她挣扎时松落,言易甚侵入她的两腿间,十指相扣地把她按在床上。
大片笼罩自己的阴影让她不安。
许尤夕剧烈喘息,她听言易甚带点戏谑意味地说:“先不说烛烛是我的孩子,就你那个抛弃你,让你挨我十年操的妈妈,你怎么说得出来这话的?你要是只给得出这一个理由,我就操死你。”
话很难听,许尤夕心里刺疼一阵,在言易甚不耐烦地要压下来的时候。
她开口了:“这十年,我连一点你的尊重都没得到…不是从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想离开你,几年前,你当着卫染的面操我的时候,我恨不得通过死亡离开你。”
言易甚沉默了,他感觉现在就像是幻梦中听她说了这么一席话。
可是他看见她漂亮的眼睛里滚出晶莹剔透的珠子,他用手指去拭,那温度和触感都惊人的真实。
他企图反驳她的这句话:“刚刚开始我对你不好,是因为你欠了我一大笔债,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两个亲人也没了,身边只有你,所以我才…”
才会把她丢上床?把她肚子操大?怎么都不愿意她离开自己?
换言易甚想不通了。
许尤夕哭得更狠,她捂住自己的脸,泪水打湿着她的耳朵,整个身子颤抖起来:“我…我知道伯父伯母离开人世的时候…我…我想着还不如和他们一起去死…”
当时她得知伯父伯母的死讯,恍惚间就已经爬过阳台护栏。
她是突然想到了言易甚,想到了那个将要回国的堂兄,才默默地原路返回。
她是他仅剩的亲人,所以她要留下来陪他。
当她发现回国后厌恶着自己的言易甚,她感觉自己好像没有选择留下,而是一脚踏空,血肉碎了一地。
这种把自己摔碎的感觉,在他强奸她的时候最强烈。
言易甚感到烦躁不安,他用力地抱紧她,咬上她的脖子,企图从她身上得到些安抚。
许尤夕被咬疼了,她在他怀里抖得更厉害,冒了一身薄薄的香汗。
“我赎罪了,我给你生了烛烛,伯父伯母说他们不怪我了,我给你生了烛烛……”
她说着,自发地平静了下来,她像是做梦似的呓语:“只有烛烛不够吗?那哥哥,我再给你生一个宝宝好不好?算我还清了好不好?”
许尤夕主动蹭他的身体,隔着浴巾在凸起上扭动柔软的腰肢。
就在他把她压回身下,将那怪物捅入湿嫩紧致的小穴,两人都感觉是在梦中。
像是发泄不满,言易甚操得很深很深,她的小肚子鼓出小包,他又对着小包揉了几下。
许尤夕疼得脸色发白,她极力地吸气让自己放松身体,却还是把言易甚夹得皱眉。
“我答应和你离婚,烛烛也归你。”
他说话的时候,许尤夕的眼睛里刚好起了湿雾。
不然她一定能看见他的脸上首次出现了落寞和无奈。
然后她才会猜到一个可能:言易甚动心了。
那个鼓包消了下去,许尤夕往下看,看见他抽出了些许,许尤夕有些不解,就被他压住啃咬唇舌。
她在言易甚调转攻势到了她的那对嫩乳时,被咬得又疼又痒的奶头,让她想张嘴求求饶。
可她突然想到言易甚总把她的求饶当做一种鼓励他更凶更狠地咬下去的情趣时,她的求饶转为一句话。
“没有我,哥哥你就可以去找真正喜欢的人了。”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胸口还在疼。
好奇怪啊,她为什么想离开他,又希望他身边不要有别人呢?
许尤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自私鬼吗?是嫉妒狂吗?
她想回到说这句话的时候,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
然后她听见言易甚很松散地回复:“你怎么还说得出这样的蠢话?”
如果十年前他没有把许尤夕丢上床,他估计到现在,也不会有真正喜欢的人。
但可以设想,这时的他身边可能会有一个联姻的妻子,试管出来的小孩。
而他依旧爱不上任何人,却可能会在一次巧合下,见到那个阔别多年的妹妹,移不开眼睛的同时,吩咐着身边的人:“那个人谁都不许碰。”
冥冥之中,他相信唯一有资格得到她,占有她的人,只会是自己。
他露出一个象征着危险信号的笑脸,烫人的指尖在她的脖颈滑走。
许尤夕怕得止住了呼吸,预测在下一秒自己的脖子就会被他掐住,掐到濒死才松开。
她还是不愿意说出求饶的话。
言易甚被脑中的两种指示拉扯着迟迟不动作。
一种让他赶紧动手,掐住仿佛稍微收力就会断掉的脆弱的脖子,让她知道惹怒自己的下场,以后再也不敢对他说出这种话。
另一种却不允许他做出暴行,好像他只要敢那样做,她就会彻底离开自己,再也不愿意陪在自己身边。
最后也没有那么做,理智占了上风。
言易甚的手掐住的是她的那截腰,把狠劲发泄在了下面相连的地方。
肉体快速碰撞的声音和压抑的哭音混合在一起。
之前从来不会为此停止的言易甚停了下来,他把高耸的物件弄出来,抱着她进了浴室。
热水从头顶直下,被紧紧圈住腰肢的许尤夕挂在他身上,断断续续吸入的湿热让她很想蹭蹭言易甚。
她浑身都没力气了,还想让听不出字句的声音从自己的喉咙慢慢流泄。
言易甚很高,也就有一双与身高相符的大手,很美观的手,指节修长,骨节较粗,给冷白色的手增添了色气。
那双大手揉搓着她发着莹白光芒的肩头,又往下揉她单薄的背。
许尤夕听见他很轻的一声叹气:“我给你一次机会,你和我说清楚原因。”
他没有抱着她淋浴太久,很快就扯了条干浴巾给她,把她抱进房间。
裹好浴巾的许尤夕看见他也扯了一条用来遮住下半身的光景。
那肿胀粗硬、丑陋的怪物依旧保持着兴奋的状态。
许尤夕不由自主地双腿发软,结合他刚刚的那句话,她就盯着他那根被浴巾遮上后,还是明显凸起的那块。
“我的鸡巴好看吗?让你一直盯着,哪有人像你一样,说要离婚,却还盯着前夫鸡巴移不开眼的?”
桃粉的脸蛋彻底通红,但很快,她的脸色一下变白。
她以为还要多纠缠一下,甚至说自己要吃些苦头。
可是,他就这么平静地带着自己洗了个澡,自称起前夫。
她一时间不知道是失落多还是开心多。
但可以确定的是,听出他愿意离婚的意思,让许尤夕很高兴。
“好了,该你说说原因了,我想不明白,是什么让你一直在找机会离开我?”
言易甚用手抬起她的下巴。
比最青涩时的她还要漂亮,还要可怜,看了十年越看越喜欢,越看越想亲吻。
她从十八岁起给自己操了,可怜巴巴地对自己一见钟情,到底是怎么选择要离开的?
被拉上窗帘的房间里开了灯,灯光从上倾斜了下来,言易甚俊美的脸上分布了几块阴影,他的眼睛里又没有属于人的温度,恍若神邸。
许尤夕时常会看着他,混乱的想:神不给人降福,却选择拉她下地狱吗?
她没有偏移视线,声音还是有些颤抖,她说:“我不是只有你了,我有妈妈,有烛烛。”
言易甚听她给的这个原因,有些恼火,突然压低身子,和她接吻。
侵略的意图太过明显,被疯狂汲取氧气的许尤夕死命推他,因为慌乱忘了呼吸,她更缺氧了。
她身上的浴巾就在她挣扎时松落,言易甚侵入她的两腿间,十指相扣地把她按在床上。
大片笼罩自己的阴影让她不安。
许尤夕剧烈喘息,她听言易甚带点戏谑意味地说:“先不说烛烛是我的孩子,就你那个抛弃你,让你挨我十年操的妈妈,你怎么说得出来这话的?你要是只给得出这一个理由,我就操死你。”
话很难听,许尤夕心里刺疼一阵,在言易甚不耐烦地要压下来的时候。
她开口了:“这十年,我连一点你的尊重都没得到…不是从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想离开你,几年前,你当着卫染的面操我的时候,我恨不得通过死亡离开你。”
言易甚沉默了,他感觉现在就像是幻梦中听她说了这么一席话。
可是他看见她漂亮的眼睛里滚出晶莹剔透的珠子,他用手指去拭,那温度和触感都惊人的真实。
他企图反驳她的这句话:“刚刚开始我对你不好,是因为你欠了我一大笔债,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两个亲人也没了,身边只有你,所以我才…”
才会把她丢上床?把她肚子操大?怎么都不愿意她离开自己?
换言易甚想不通了。
许尤夕哭得更狠,她捂住自己的脸,泪水打湿着她的耳朵,整个身子颤抖起来:“我…我知道伯父伯母离开人世的时候…我…我想着还不如和他们一起去死…”
当时她得知伯父伯母的死讯,恍惚间就已经爬过阳台护栏。
她是突然想到了言易甚,想到了那个将要回国的堂兄,才默默地原路返回。
她是他仅剩的亲人,所以她要留下来陪他。
当她发现回国后厌恶着自己的言易甚,她感觉自己好像没有选择留下,而是一脚踏空,血肉碎了一地。
这种把自己摔碎的感觉,在他强奸她的时候最强烈。
言易甚感到烦躁不安,他用力地抱紧她,咬上她的脖子,企图从她身上得到些安抚。
许尤夕被咬疼了,她在他怀里抖得更厉害,冒了一身薄薄的香汗。
“我赎罪了,我给你生了烛烛,伯父伯母说他们不怪我了,我给你生了烛烛……”
她说着,自发地平静了下来,她像是做梦似的呓语:“只有烛烛不够吗?那哥哥,我再给你生一个宝宝好不好?算我还清了好不好?”
许尤夕主动蹭他的身体,隔着浴巾在凸起上扭动柔软的腰肢。
就在他把她压回身下,将那怪物捅入湿嫩紧致的小穴,两人都感觉是在梦中。
像是发泄不满,言易甚操得很深很深,她的小肚子鼓出小包,他又对着小包揉了几下。
许尤夕疼得脸色发白,她极力地吸气让自己放松身体,却还是把言易甚夹得皱眉。
“我答应和你离婚,烛烛也归你。”
他说话的时候,许尤夕的眼睛里刚好起了湿雾。
不然她一定能看见他的脸上首次出现了落寞和无奈。
然后她才会猜到一个可能:言易甚动心了。
那个鼓包消了下去,许尤夕往下看,看见他抽出了些许,许尤夕有些不解,就被他压住啃咬唇舌。
她在言易甚调转攻势到了她的那对嫩乳时,被咬得又疼又痒的奶头,让她想张嘴求求饶。
可她突然想到言易甚总把她的求饶当做一种鼓励他更凶更狠地咬下去的情趣时,她的求饶转为一句话。
“没有我,哥哥你就可以去找真正喜欢的人了。”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胸口还在疼。
好奇怪啊,她为什么想离开他,又希望他身边不要有别人呢?
许尤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自私鬼吗?是嫉妒狂吗?
她想回到说这句话的时候,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
然后她听见言易甚很松散地回复:“你怎么还说得出这样的蠢话?”
如果十年前他没有把许尤夕丢上床,他估计到现在,也不会有真正喜欢的人。
但可以设想,这时的他身边可能会有一个联姻的妻子,试管出来的小孩。
而他依旧爱不上任何人,却可能会在一次巧合下,见到那个阔别多年的妹妹,移不开眼睛的同时,吩咐着身边的人:“那个人谁都不许碰。”
冥冥之中,他相信唯一有资格得到她,占有她的人,只会是自己。